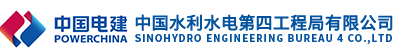凍土與炊煙的雙向奔赴 |
|
|
|
|
灤平的凍土在暮色中泛著鐵青色,我裹緊沾滿水泥灰的棉衣,在地下洞室的鋼架間穿行。手機震動的瞬間,仿佛觸到了臘月屋檐垂下的冰凌——母親來電的號碼亮起時,竟帶著熟悉的灶火溫度。 “孩,后坡的苜蓿冒芽了,苦菜和蒲公英都水靈著。”她的聲音像被風吹散的棉絮,夾雜著沙沙的電流聲,“地軟泡了兩盆,包了洋芋包子......要不,給你寄些?”我的手不自覺地收緊,仿佛能透過這小小的屏幕,摸到母親那布滿老繭卻溫暖依舊的手。那小心翼翼的尾音,像幼時我踮腳夠不到糖罐時,她伸出援手前的試探。 安全帽上的水珠突然變得滾燙。兩千多里的路程,橫亙在我和母親之間。然而此刻,她的聲音卻如此清晰,近在咫尺。我的思緒飄遠,越過燕山的峰巒,穿過廣袤的原野,回到了渭北塬上那座飄著炊煙的小院。關中平原上,母親定是天未亮就踩著晨霜出門。她蹲在苜蓿叢間,枯枝般的手指拂過嫩葉,挑揀最鮮嫩的掐下;在布滿裂紋的青石板上,將蒲公英的鋸齒葉片細細洗凈;案板上的面團被揉成滿月形狀,裹進金黃的洋芋絲、黑亮的地軟,還有切碎的蔥花——每一道褶皺里,都藏著我對家的思念。 “路太遠了,媽……”我的聲音被通風機的轟鳴撕碎。電話那頭傳來瓷碗相碰的輕響,像是母親慌忙放下手中活計:“早備好了!干冰鋪得厚厚的,泡沫箱纏了六層保溫布,明天一早我就拿到快遞站,他們早上七點發車,我今天專門去問了……”她的語速越來越快,生怕我拒絕,“就當給媽個念想,你收到,我心里就踏實。” 如今,母親在電話里小心翼翼地問我要不要寄包子,我卻猶豫著是否要拒絕。那不僅僅是包子,更是母親滿滿的牽掛和思念啊。我忍住眼中的酸澀,輕聲說:“媽,寄吧,我想吃。”母親在電話那頭笑了,笑聲里充滿了欣慰和滿足。 記憶中,家鄉的春天總是格外絢爛。漫山遍野的苜蓿、苦苦菜和蒲公英,像是大地灑下的翡翠。小時候上學,每天晚上母親都會變著花樣給我做早餐。春日清晨推開吱呀作響的木門,便能聞到從廚房飄來的陣陣清香。薺菜餡的餃子在清湯里臥著,蝦皮的鮮味與薺菜的清香相互交融;香椿攤成的金黃雞蛋餅,咬一口,滿是春天的味道;榆錢拌著面粉蒸得蓬松綿軟,甜絲絲的,直沁心脾。 母親揉面的樣子一直印在我的腦海里。她的手因常年勞作而粗糙,卻有著神奇的魔力。白花花的面團在她手中翻轉、揉搓,不一會兒就變得光滑而有韌性。包洋芋的軟包子時,她的動作嫻熟而又輕柔,每一個包子都飽含著她的愛。 待蒸籠掀開,白霧繚繞間,母親總是先夾起最飽滿的一個,放在嘴邊輕輕吹涼,然后遞到我嘴邊,笑著說:“快嘗嘗,燙不燙?”她看著我大口吃著,眼睛里滿是溫柔和滿足。那些被母親的愛包裹著的早餐時光,是我童年里最溫暖的記憶。 后來,我離開家鄉,到外地上學、工作,與母親相聚的時光越來越少。每次打電話,她總問我吃得好不好,叮囑我要照顧好自己。而我,總是在掛斷電話后才想起,似乎很少關心她過得怎么樣。 掛斷電話的剎那,洞室深處傳來爆破的悶響,驚起滿室塵埃。手機相冊里,母親站在老家屋檐下拍的照片微微泛黃,藍花圍裙在風中鼓起,如同一片湛藍的海。她那花白的頭發在陽光下閃爍,仿佛覆蓋了一層薄霜,顯得格外醒目。每根銀絲都訴說著歲月的故事,記錄著無數個清晨她在廚房忙碌的身影。此刻,那方裝滿野菜與包子的泡沫箱,正載著故鄉的月光啟程,穿越秦嶺的云濤,跨過黃河的冰裂,像一封帶著體溫的情書,撲向我棲身的鋼鐵森林。 三天后的清晨,快遞員抱著箱子出現在項目部。打開的瞬間,寒氣裹挾著麥香、野菜的清苦與地軟的醇厚撲面而來,恍若跌進了母親的圍裙兜。蒸籠掀開的剎那,白霧騰起,模糊了鏡片,也模糊了時光的界限。咬下第一口,滾燙的餡料在舌尖炸開,綿密的洋芋、柔韌的地軟、帶著陽光味道的蒲公英,將我拽回無數個被母親的灶臺溫暖的清晨。 這跨越兩千公里的包裹,不僅是母親對兒子深深的牽掛,更是凍土與炊煙的美麗邂逅,是鋼筋森林里突然綻放的、帶著露水的鄉愁。在這瞬息萬變的世界里,唯有親情永恒不變,如同那一縷縷炊煙,永遠飄蕩在我心中最柔軟的地方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